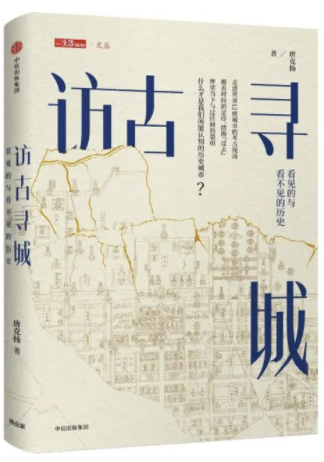原载于《信睿周报》第23期
2009年,古根海姆博物馆想在中国寻找一位合作者,策划一场他们瞄准的“未来主题”的建筑展。对于国外博物馆而言,筹划一个展览的时间动辄四五年,要想影响更久远,起码也得再看远十年,所以他们所说的未来,也就是多年后的此刻——我们正在面对的现实。作为这件事的参与者,我的印象很深,他们意欲的题目本是“城市的未来”——但最后他们划掉了“城市”,换上了“乡村”。
可是,在中国,对“乡村”并没有统一的定义。我们平时常听到的与“乡”有关的现代汉语词汇,包括“乡村”“农村”“乡镇”“乡土”“故乡”,含义都并不明确……如果你只是听说一个人在搞“乡建”,并不能因此就多看他两眼。因为他的“乡村建设”,有可能只是一个在中国国情下来自不同委托方的“活儿”罢了,纵使白墙黑瓦,也可能只是个不折不扣的都会商场。在江南,一些城镇化程度较高的“村”早已失去了既有的“村镇”形态。相反,西部地区的某些大城市,可能比青浦、吴县(现苏州市吴中区、相城区)、南浔……更像农村一些。
事实上,把“乡”作为“城”的“负像”来分析或许更加贴切——我们心目中的“城”是什么样的,“乡”就是它的反面。什么是中国语境中的“城市”?这本身就是个问题。对大都会的推崇,尤其是把特定的城市建筑形态和“地方”的大概念联系在一起——比如,谈起北京就是天安门,提到上海便想起外滩的那一排西洋大厦——是一种现代才有的现象。
不确定“城”也就无从定义“乡”,甚至“故乡”也无从谈起。其实“故乡”的观念一直在发生变化,“故”可以特指过去,“乡”是进城之前的所在,说白了就是“老家”;也可以理解为今日对一种更理想的人居环境的乡愁,是西方的现代化模式之外的替代方案——这不,从工业革命开始,西方人自己就已反思他们的“(大)城市”观念了。长久以来,人们已经意识到“城-乡”模式的文化间差异,比如,在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等人看来,中国的“城-乡”面貌并不存在显著差别,马克斯·韦伯则指出,“中国城市居民在法律上属于他的家庭和原籍村庄”。

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
[美] 施坚雅 / 著
史建云、徐秀丽 / 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在当代中国探究这些概念,表面上看是人居环境的更新,内里却是两类城市文明的冲突。
“故乡”这个词本身就已经暗示着空间-时间的双重“疏离”。“故乡”即“故”乡。西方文化中差堪比拟的一个例子是“离散”(diaspora),比如犹太民族的出走。中国历史上也有类似的现象:大大小小的“衣冠南渡”,包括笔者在内的很多南方人,据说祖上都来自北方某处。这类现象中,普遍存在着“原有”的种族起源(故乡)和“现居地”(散居地)之间的“小”“大”关系,或者鲜明的地方文化与其模糊的原型的关系。它的结果就是彰显了“客”家的属性及其聚落的特征,比如大家都熟悉的永定土楼。
“故”乡的概念确立过程同样包含了时间的因素。正是由于社会历史的演进,乡村才从文明的中心舞台上退到了背景之中。今日人们对于乡村建设的热情,很大程度上来自幻想之中现代化前理想社会引发的乡愁——是永远的“桃花源”。但“故”乡并不一定就落在今日之“乡村”,20世纪以来,后者的图像在中国人心中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传统中国的“城-乡”并不单指建筑和景观的对立。这表现在两方面:其一,“乡”也可能是城市,行政上与其平行或重叠,例如隋唐长安城,以朱雀大街为界分别由长安和万年两“县”管理,两县管辖的范围既包括城内也包括城外;其二,“城-乡”的面貌并没有显著的区分,虽然大多数城市都在城墙以内,但是城市里也不乏乡野景色(想想费穆和田壮壮的《小城之春》),而某些大型聚落虽然处于城外乡村,但和城内的里坊并无实质的差别。所以,以现代的标准来检视古代城市的发展,大概会有身份暧昧的“都市乡村”或者“乡村都市”两类概念:一类是城市里内含的乡野形态,比如长安的“围外地”,以及某些历史时期城市中存在的“城中村”;另一类是接近城市标准的“村”,比如很多人都去过的徽州西递、宏村。
 安徽宏村。(图片来自Unsplash @jerryyileibao)
安徽宏村。(图片来自Unsplash @jerryyileibao)
硬要到今天的乡村去“倒推”甚至重新“发明”一个新农村,就会遭遇传统和现实之间的三重尴尬:现代文明和经济发展强力拼合起来的某些乡村“开发区”,没有任何传统社会的聚合力;很多“桃花源”是用当代西方之“城”的模式套中国既有之“村”,可是“村”天然就缺乏一个持续而稳定的中心;在大城欠缺、小村镇发达的地理区域,比如我的故乡江南,并不容易判定“城-乡”的物理边界。
不同历史时期的“故”乡经常意味着不同的“城-乡”关系。例如,按照传统说法,我的“原籍”并不是出生地安徽芜湖,而是肥东某“乡镇”,那里也是大多数中国人观念里标准的“老家”,即宗族祠堂所在。因血缘关系而建立起来的这种底层社会组织,是当代“乡村建设”理应倚重的重要结构。但是,作为长江沿岸重要的商贸港口,芜湖的流动人口占比极大,我的父母都是外来移民,他们甚至从来都没有回过“原籍”,传统的“城-乡”邻里层级在此发生了断裂。如果说,我父母那代人的这种“背井离乡”尚属偶然,那么对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我这一代人来说则已是普遍情形,是农业社会结构现代重组的必然结果。“老家”本是具体的,今天却慢慢成了“城市A现居所-城市B出生地”的双城模式,城市人和他们原居住地的土地之间,已经既无法律关系也无经验联系。“故乡”所依据的城-乡空间本身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人和土地的二维关系首先被置换成了城市中含混而抽象的物权概念,随之,静态的使用权结构(只有“里”“外”)又被新的三维空间构成重新解释了一遭。某些乡村地址居然已经从地图上彻底消失了,通过“零存整取”式的开发置换,传统的里巷成了新的复合型“空中社区”。回迁居民中很大一部分并非原址居民,即使那些原地安置的老住户,他们的住地和原地址也难以精确地对应,因为整个居住结构都已被颠覆重来——这是一种颇为奇特的中国现象。
如果说今天的乡村建设正在向一种未及定义的新“传统”回归,那么,我们究竟需要回归到什么“样”的“故”乡?显然,这种假设的回归是不存在的,因为改变了特定时代或空间的前提,也就取消了这种图像。我们企图得到的过去时代乡村的表象,就仿佛电子望远镜“望见”的数十万光年外的星球,它们其实是属于“过去”的图像,貌古实新,貌中实西。“光年”这个单位好,因为一种文化突然跨越到另一种文化的空间距离,也约等于它们之间的“时差”。
既要空调卫生,又要山水野趣,我们当下的“乡村建设”,其实是重新开始,而未必是向过去致敬。
1984年,在重版1947年出版的《乡土中国》一书时,费孝通明确地指出:“这里讲的乡土中国,并不是具体的中国社会的素描,而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它并不排斥其他体系同样影响着中国的社会,那些影响同样可以在中国的基层社会里发生作用。搞清楚我所谓乡土社会这个概念,就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具体的中国社会。”

乡土中国
费孝通 / 著
中信出版集团,2018-12
由此可见,社会学家费孝通提出的“乡土”并不等同于地理学意义上的“乡村”,而是现代政治经济学的某种概念,就仿佛“上层建筑”“经济基础”所借用的粗放的空间譬喻——“概念在这个意义上,(只)是我们认识事物的工具。”费孝通没有,对他而言也不需要在此说明的是“底层-顶层”关系的恰当比喻或许是细胞之于血脉,或沙子水泥之于混凝土,而不是不同楼层的“底层-顶层”。
或许因为现代中国建筑学内含的形态学敏感,也或许由于长久习惯的一种非此即彼的两分法,更或许源于上述中国当代社会对“故乡”的重新定义,在建筑领域内,“乡土”慢慢成了和城市对立并彼此脱离的范畴,“城-乡”的关系与“底层-顶层”的社会结构图解错位了——社会学和管理学意义上的“顶层”和“底层”实则是一体两说,今天提出的“城乡规划”却真的是城市-镇-乡-村庄的金字塔体系。在这个时刻,“城-乡”的疏离已经成了不可逆转的现实。
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建筑学的“城-乡”分离,同时伴随着笛卡儿的哲学理念,将“城-乡”在数学指标上最终统一起来,成为今日“城乡一体化”的理论基础,这恰和中国“城-乡”两分对立的现代情形构成矛盾。例如,2007年颁布的新版《城市规划法》和《物权法》,强调了城乡之间的“统筹”,也就是在空间上达到城乡规划“一盘棋”。在理想状态下,中国未来的区域发展将可以进行系统和总体调控,层级间平滑转移,不再有行政体制的人为分割。按照城市规划法制定者的愿景,这种“平等对待”将进一步促进“城乡一体化”的进程——正如美国规划史上有名的“六英里”法[1]或者英国人测量印度采用的“三角形测量法”,将一种人为的逻辑不加区别地适用于两种不同的人类生存环境,意味着直观的和相对的古典世界终于让位于抽象的和绝对的现代思想。
有意思的是,既然有了以上重新阐释的“乡土”概念的引导,中国建筑院校“乡土建筑”的调查方法本该异常看重社会学方法才是,但似乎迄今为止,大多数“乡土建筑”的调查成果仅有与上述规划趋势相适应的大规模乡村“测绘”。这种“测绘”偏好于建筑结构或村落布局,倚重于笛卡儿式的建筑制图(平面、立面、剖面)——是意向宏阔的“本地做法”,止步于粗线条的“本地风格”的勾勒。而这种“本地风格”在成为墨线以前并不清晰存在——“徽州民居”就是这种大规模的“乡土建筑”调查最著名的成果之一。“风格”在此既是本地的,往往又是无特殊社会“内涵”的,只能潜藏于“如画”的景观之中;与位于城市的“民族风格”和“官式建筑”相比,特定的“乡土建筑”和特定的社会礼仪、社会心理的联系更加松散隐蔽,至少对建筑师而言,后者是一片甚少有人去探索的深水区。
“礼失求诸野”,在很多时候,当代素朴的“乡土”建筑还意味着对现代文明具有抵抗意义的“传统”,它在肯定了乡村的传统美学价值之余,将其物理容器也连带作为不可能再存在的“传统”(“故”乡)的载体。和上述由对立的空间意义(“城-乡”)转向均一的数学指标(“城乡一体化”)的过程类似,对于过去的乌托邦的想象,也导致了费孝通拈来的抽象概念“工具”(乡土中国)逐渐被建设者固化为现实的人居“范式”(“山水城市”)。
舶来的西方建筑学专业改变了乡村建设的基本面貌,它甚至也再次确立了物理形态优先的“城-乡”定义。我们看到,这一过程经历了不同历史时期的逆转和反复,这些逆转和反复也和所属区域的发展浪潮密切相关,反讽的是,今日的“故乡”或者说中国理想人居的图像,最终是通过乡村建筑“类型”(type)这一外来方法“建设”出来的。
物理形态优先的“城-乡”定义总是依附某种象征含义,就好像城墙对古代“城市”的意义一样:“……当前对中国古代城市的城墙存在一种普遍的误解,即认为城墙是中国古代城市的必要组成部分,或者认为中国古代绝大部分时期,地方城市都修筑城墙……”[2]按照有城墙的“城市”中心的观念,城市史是城市向郊区和乡村逐渐延伸的进程,其结果必然导致离心状的均匀“蔓延”,大城派生出小城,但事实并非一定如此。近代以来,江南也出现了数次毁弃城墙的机遇,新的政治气候和经济发展需求,让城关连接部和城郊水滨贸易地带,也沿着自己的功能逻辑自由延展,随着经济需求的“城-乡”混融或说建筑-景观的混合,成为最终的城市化来临之前另一种形式的城乡一体化。
如果说,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西方殖民者将中国城市误读为乡村,是对这种“城-乡”混融的一次总结——景观统合了城市,那么一百年后的“城乡一体化”中,又是“乡村”倒过来影响了城市的面貌——但这次却是以相反的方式:建筑征服了景观。
 吴冠中作品《安徽水乡》(图片来自网络)
吴冠中作品《安徽水乡》(图片来自网络)
还是以我的老家为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芜湖是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前哨”,它的城市建筑本是无甚特色、风格混杂的,由于徽州文化和“安徽”建制逐渐加强的联系,或许也由于强调山墙面的徽州建筑较好和现代建筑功能融合,“后院”徽州保存完好的建筑逐渐成为当代芜湖城市建设的标准式样。就像挂满中国的“吴冠中式”绘画一样,白墙黑瓦的乡村建筑甚至逆袭了城市,为它带来了先前所不具备的“万能疗效”。
较早对徽州住宅做系统调查的是南京工学院(今东南大学)的相关课题组,张仲一等人编写的《徽州明代住宅》可以被看作同时期的中国建筑研究者刘敦桢1956年发表于《建筑学报》的《中国住宅概说》之后的延续性成果,由此之后,徽州建筑才受到广泛的关注。步入新世纪,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编辑出版了《地方传统建筑(徽州地区)》的标准图集(图集号03J922-1),但早在1991年,“在全国性旧城改造风潮影响下”,本来相距甚远的“徽派风格”重修了芜湖市的十里长街,“徽派风格”的适用范围也从“原徽州地区”扩展到“适宜营造徽州地方传统建筑的(整个)江南地区”[3]。借助普适的(西方)建筑学方法,过去的城乡差别、地区差别,现在变得没那么重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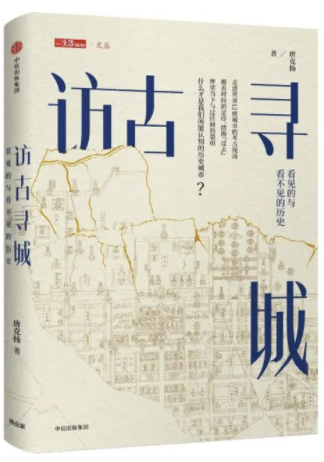
在这幕“城-乡”暗渡的戏剧之中,西方建筑的类型理论(typology)起到了黏合剂的作用——继“四合院”的城市模式之后,当代建筑师试图将乡村的“空间”予以抽象,认为传统中的空间“类型”具有自我更新的能力。一部分建筑师提出由大及小的地形、聚落、空间三件套概念,这原本是强调特定环境对于建筑类型的系统影响,但为了加强“类型”的普适性,他们又不能不夸大“城-乡”环境跨越地域的共性,仿佛它们都是冥冥中某种“算法”的产物:“三者(其实)是同一事物在不同的三个层面上的表现”“……任何聚落空间的背后都存在有某种潜在的非定形的力……这个力具有相对的稳定性”[4]。此“力”的概念是非历史的,唯借力于普遍的理想的“故乡”意象,才可以无视今日“城-乡”在政治学和社会学上的差异。应该说,这样的转变并不是孤例,而是大量地出现在以“景观地建筑”或“园林建筑师”自况的当代中国建筑师中。由“城市景观”到“乡村建筑”,从“城市乡村风格”而至“乡村(用城市的方法)再造”,可以看成是城市-乡村-城市的一次语义循环,它既是物理类型的转适,又是文化意义的再生。今日中国巨大的城乡差别,本是近代化带来的新的后果,我们大可预言,随着西方城市观念而改变的中国城乡秩序,将会让“城市”更像(西方的)城市,而原住民让位于旅游者,则使原本中性的“乡野”更似无人(景)区。
但“故”乡有可能再“还魂”,通过热心于“作品”“建造”的建筑师眼中抽象的乡村“类型”,它们将重新回到我们视野的中央。
[1] 1785年,美国国会通过《土地测量法令》(Land Survey Ordinance),推出正方形镇区制度,规定镇区边长为六英里,划分为36块土地,每块土地面积为一平方英里。——编者注
[2] 《古代城市形态研究方法新探》,成一农 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66-244页。[3] 《地方传统建筑(徽州地区)》,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 编,2003年,图集号03J922-1。[4] 《传统聚落结构中的空间概念》,王昀 著,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年。